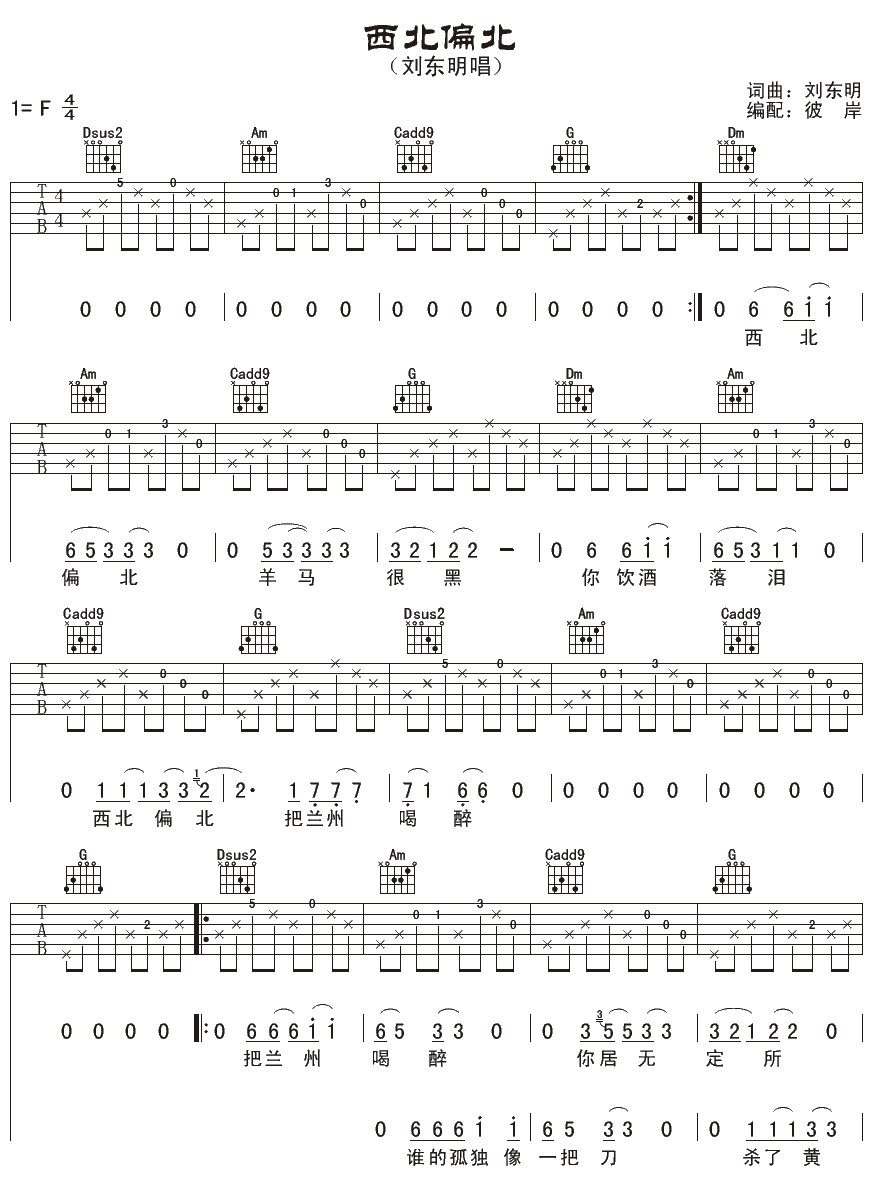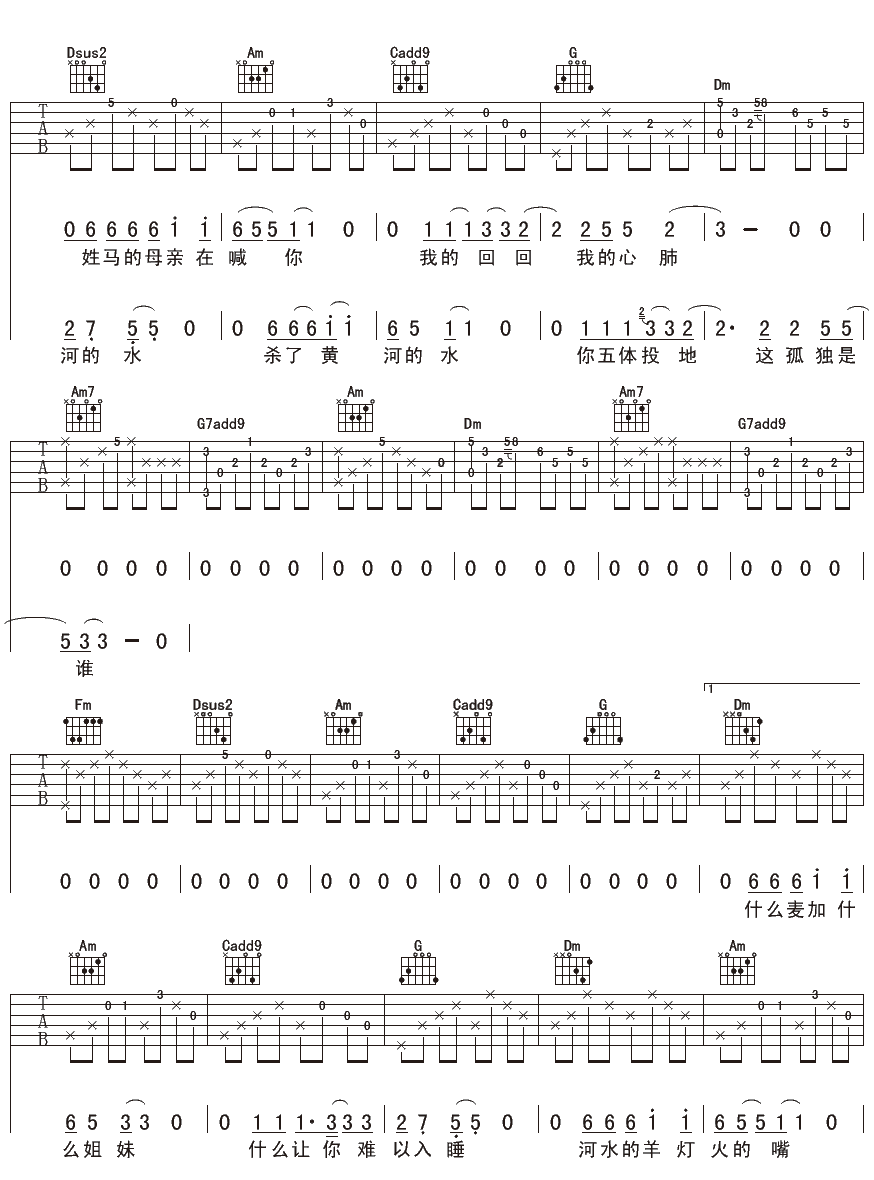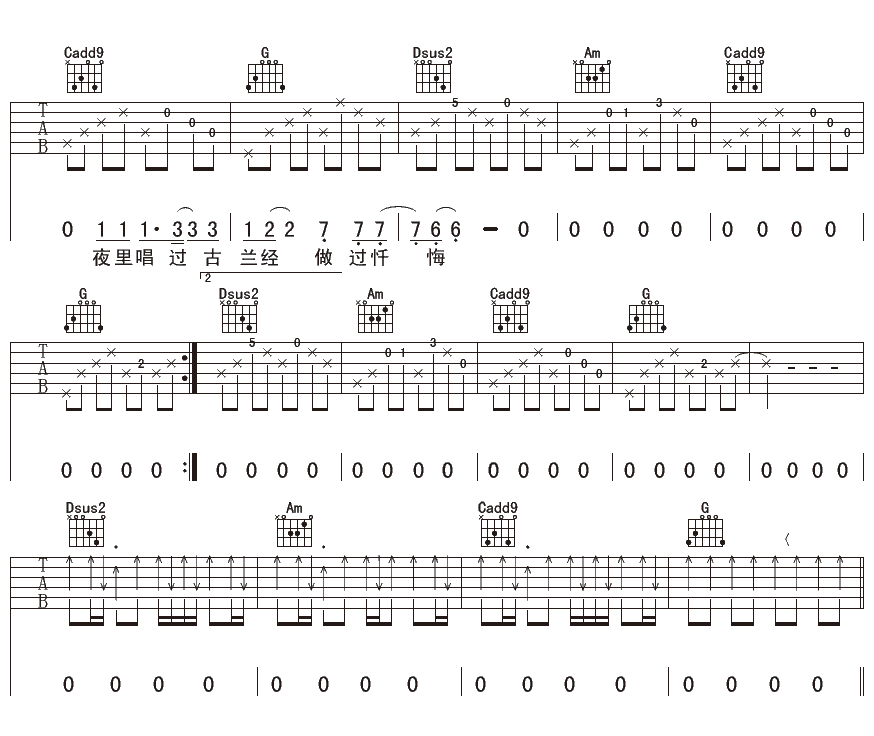《西北偏北》以苍凉的地理意象为底色,铺陈出生命迁徙的孤独图景。歌词中反复出现的方位词构成精神坐标,黄河远去的意象既是地理层面的流动,也暗示着时间不可逆转的流逝。荒原与野花并置的悖论美学,揭示生存境遇中野蛮生长与残酷凋零的永恒对抗。酒馆与醉汉的市井场景被赋予存在主义色彩,醉酒成为对抗虚无的临时解药,而破碎的陶罐则隐喻着传统文化在现代性冲击下的脆弱状态。歌词中"你把忧伤画在眼角/我将流浪抹上额头"的互文性表达,呈现了两种生命姿态的诗意对话——静态的忧伤与动态的流浪共同构成了人类应对孤独的基本范式。西北风物被提炼为精神符号,马匹、石头等意象既承载着土地记忆,又转化为灵魂重量的具象化表达。最终所有漂泊都指向存在的根本命题:人在广袤时空中的微小与坚韧,如同野花在西北风中的倔强绽放,用瞬间的绚烂对抗永恒的荒凉。这种生命态度不是悲壮的抗争,而是静默的承担,在认领孤独的过程中完成对自我命运的抒情式救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