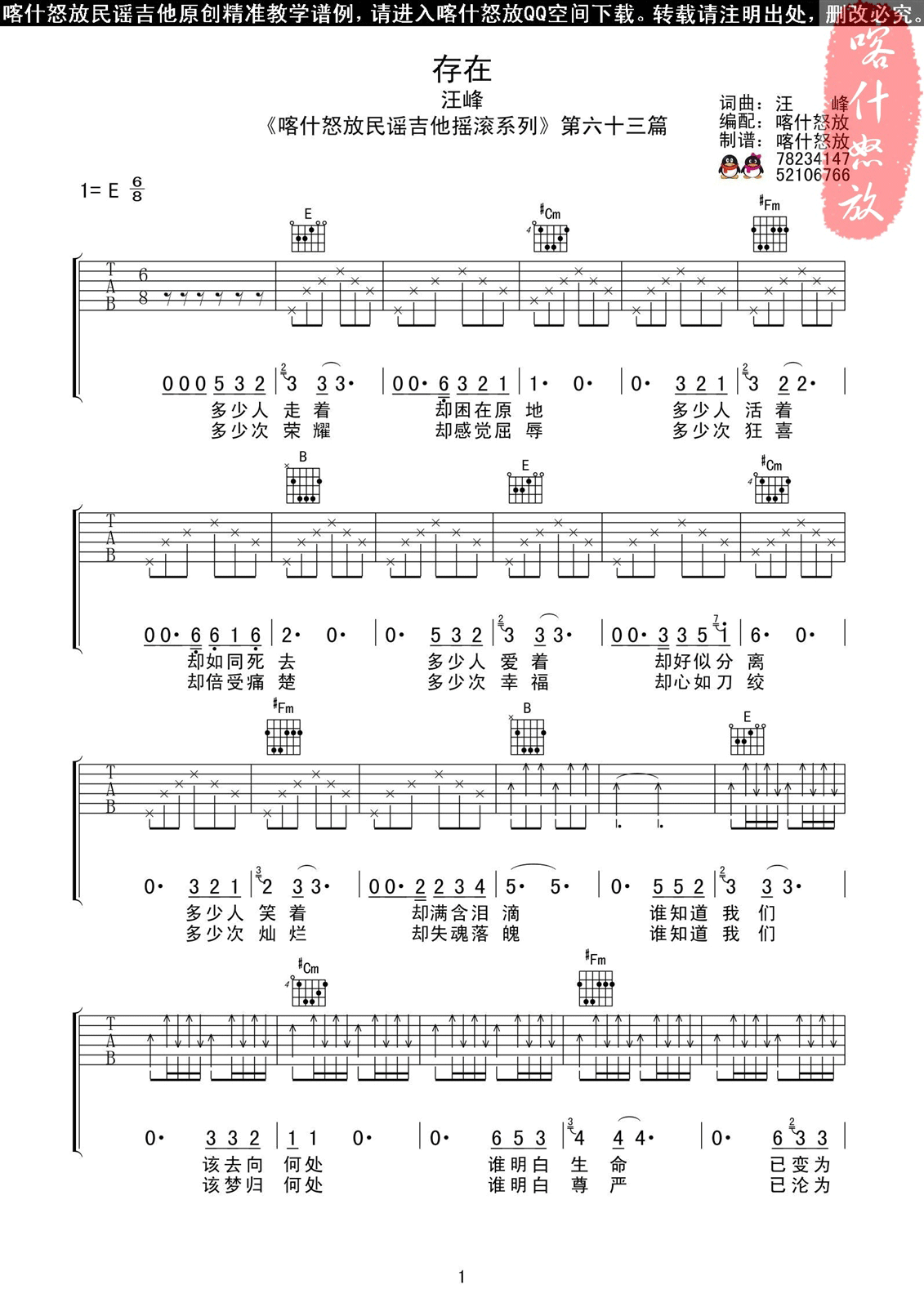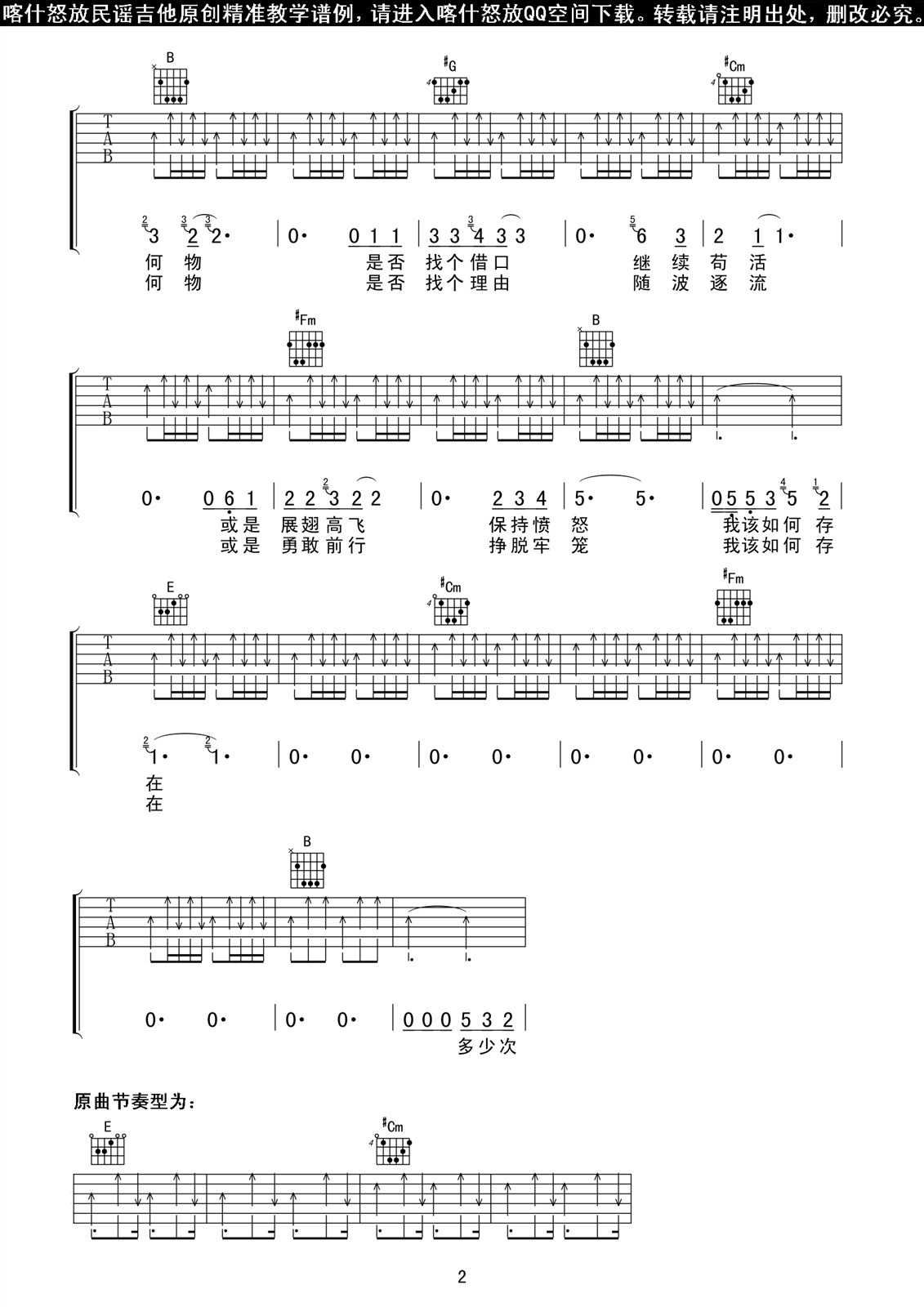《存在》以意象化的语言构建了关于生命本质的哲学追问,通过"锈蚀的齿轮""断裂的琴弦"等隐喻式意象,呈现现代人精神世界的荒芜与异化状态。歌词中反复出现的"虚无的重量"构成核心悖论,将存在主义关于"存在先于本质"的思考转化为可感知的诗歌意象,揭示物质丰裕时代的精神失重现象。"被时间碾碎的倒影"这一意象群,既指向个体记忆的碎片化特征,也隐喻历史叙事中主体性的消解过程。歌词通过"在裂缝里寻找光"的行为意向,展现西西弗斯式的抗争精神,而"未完成的歌谣"则象征着人类永恒的未完成性。文本中的矛盾修辞如"喧嚣的寂静"精准捕捉了当代生活的荒诞质感,将海德格尔"被抛状态"的哲学概念转化为具象的情感体验。最终以"灰烬里的星火"作结,在彻底的解构中保留重建意义的可能性,完成从存在困境到生命韧性的诗意转换。整首作品构成一个完整的现象学文本,用诗歌语法重新阐释了加缪"在虚无中建立意义"的存在主义命题。